
明代文獻中記載的玉蜀黍
原著:千葉德爾 翻譯:于景讓教授(科學農業 1973: 21卷5/6期) 承科學農業社社長康有德教授慨允轉載譯者說明
哥侖布發見新大陸是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二行關於玉蜀黍的記載,並有一個現在看起來是很奇特的玉蜀黍的圖。『本草綱目』,據譯者所知最早者是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金陵胡承龍的刊本。李時珍是卒於1596年。據 Bratschneider,則本草綱目的出版年度是1560~70,自哥侖布發見新大陸至『本草綱目』第一版(1596)刊印,中距40年或不到80年。李時珍記錄玉蜀黍,大概不會是在玉蜀黍傳入的當年,自記錄至刊印,中間亦有一段時期。故據『本草綱目』,則自哥侖布發見新大陸至玉蜀黍傳入中國的湖北省,其間大概不到100或不到80年。 田藝蘅的『留青日扎』,是刊印於明萬曆元年(1573)。其中記載玉蜀黍是較本草綱目為詳細。自哥侖布發見新大陸至『留青日扎』刊印,其間距離是81年。田藝蘅大概亦不會在玉蜀黍傳入當年便行記錄,而自記錄至刊印亦經一相當長的時期,故自哥侖布發見新大陸至玉蜀黍傳入浙江杭州,一定是遠少於80年。其間雖有葡萄牙人東航,而玉蜀黍傳布中國各地的期間實嫌短促。
譯者讀過方志,而沒有時間作大規模的搜索,亦沒有想到從雲南的方志讀起,並且讀線裝書搜索資料,真如披沙淘金,往往費力極多而不一定有效果。故譯者對於玉蜀黍傳入中國的知識,是止於『本草綱目』與『留青日扎』二書,而疑問始終不解。
讀千葉教授文,深驚其引用資料範圍之廣,而玉蜀黍有Persian Type, Aegean Type, Caribbean Type 之分,在我這一個讀過農學的人,亦是最新的知識。讀千葉教授文後,我的疑問,已大部份消失。試為譯出,以供有同樣疑問者參考。
據千葉教授給我的信,他不讀農,亦不會中國話,真使我這一個讀過農、會說中國話的人愧汗而無地自容。
京都大濱田稔教授先賜贈複印本,愛知大學千葉教授賜贈抽印本及參考資料,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圖書館允准任意翻閱方志及其他參考書,謹此一併致謝。
正文
|
一、 |
田藝蘅的『留青日扎』,到現在為止,一般皆以為是中國記載玉蜀黍的最古的文獻**。
萬國鼎編:五穀史話(1961)。
『留青日扎』刊於明萬曆元年(1573),(比較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還要早五年。)『留青日扎』記載玉蜀黍是稱御麥,文曰:
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稈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真異穀也,吾鄉得此種,多有種之者,吾鄉以麥為一熟。古稱小麥忌戍,大麥忌子,皆忌水也,故吳鄉低田不可種。(于按:據中央圖書館藏隆慶六年刊本第二六卷校正)。
番麥之名,大概是如『本草綱目』所說,因傳自西番之故。西番麥之名亦見於嘉靖三九年(1560)刊的平涼府志,而現今福建省的一部分亦是稱玉蜀黍曰西番麥**。故吾人對於西番麥,可視為在中國古時嘗流行於各地(于按:今江南一帶仍稱番麥)。
廈門稱番大麥,浙江南部稱番黍(據『五穀史話』)。
玉蜀黍自西部路線傳入中國之說,雖為De Candolle所否定,而在現今的中國的農學者間仍為一有力的通說**,根據大約就在此項古時的記載。
湯起麟:玉米,p.1. (1956)
『留青日扎』說番麥是舊名,今稱御麥,亦很值得注意。這一發音,自18世紀以來,嘗普及於四川雲南。萬曆四年(1576)的雲南通志所載的玉麥,與玉蜀黍通稱的御麥,是同音異字。元代末賈銘的『飲食須知』,也有玉蜀黍即番麥之名**。
如賈銘已知有玉蜀黍,則是在哥侖布發見美洲以前,中國已有玉蜀黍。『飲食須知』中,亦記有落花生:L. C. Goodrich 謂皆係後世所附加。(L. C. Goodrich,Early notic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Monumenta Serica, Vol.II,No.2,1937) 。天野元之助亦表示贊成之意。(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p. 54,1962)但就。『飲食須知』的記載方式以言,落花生是一新的項目,而玉蜀黍是附記在蜀黍項的末尾。故對於玉蜀黍或可視為蜀黍的一個品種。這不一定是指自西歐傳入的玉蜀黍。故因落花生是後代附加,而類推玉蜀黍亦是如此,不一定是很適切的。
所謂御麥,是因嘗供皇帝進食得名。故田藝蘅賈銘皆加以記載**。
參閱『五穀史話』。但筆者參考的東洋文庫藏本學海類編中的『飲食須知』無御麥云云,故這或許是『穀譜』的記載,而誤以為『飲食須知』的記載。穀譜曰:玉蜀黍一名玉高梁,一名御麥。因會經供御用,故名御麥。出西番。舊名番麥。(于按:穀譜文是由日文譯出,手頭無穀譜,故未能與原文對照)。
但是,是什麼時候、那一位皇帝吃過,則皆無說明。萬國鼎氏的五穀史話,謂:御麥是好麥之意,是元代皇室的司膳者所用之上等的麥,故與玉蜀黍是不同的麥。但筆者另有意見,筆者以為這是把玉蜀黍與薏苡(Coix)混淆後所產生的傳說**。
河南省郟縣志氣順治年間,在「玉麥即玉蜀黍」下注曰:「即光武所飯之麥」。光武帝是東漢第一代皇帝,早期流寓於河南河北。嘗有有人進獻這個麥的傳說,大概流傳頗廣。這大概是由伏波將軍馬援在南方食薏苡以為美持歸獻給光武帝這一事實所遞演而成的傳說。玉麥或御麥的形態,與薏苡者是比較近似的。如再稍逞想像,則與薏苡形態近似的玉蜀黍應當是波斯型。(于注:對於作者的這一個注,我表示懷疑。光武所食麥飯,據我的了解,是大麥飯。郟縣志的注,已是附會,而作者的說明,似附會更多。)
田藝蘅的家鄉是浙江省錢塘縣,該處的玉蜀黍,幹葉皆似稷,即皆似蜀黍(高梁)(于按:稷是現今所謂的粟,但在中國文獻中誤以稷為高梁,由來已久,說見拙作「黍稷粟梁與高梁」)。玉蜀黍與蜀黍,在幼苗時期,雖是專門家,亦不易鑑別。成長後,玉蜀黍中,有葉伸展作左右對稱形,莖葉粗剛作深綠色者,這與比較上是淡綠色而有纖細之感的蜀黍,就可以區別了。葡萄牙人攜入日本的Caribbean型的玉蜀黍品種,明治以後傳入日本北部的北美型的玉蜀黍,該項形態甚為顯著。在形態上,到最後為止,仍與蜀黍不易辦別的玉蜀黍品種,是波斯型。一般以為這是亞洲特產的很原始的一型**。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田藝蘅喜愛農村生活,是十分了解農業的人物,故對於蜀黍與玉蜀黍的區別,應當是知道的。如是,則因波斯型的玉蜀黍是沿著波斯──希馬拉耶──爪哇山系而分佈**,故田藝蘅鄉里的玉蜀黍是西方傳來的品種,此種可能性極大,其記載云鬚如紅絨,故其花柱大概在抽出時就是紅色。
S. Nakao 1958 Transmittence of cultivated plants through the Sino-Himalayan route,in H Kihara (ed.) Peoples of Nepal Himalaya. p. 397~420, Kyoto.
雲南省蒙北縣稱曰紅鬚麥的植物,據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是指玉蜀黍。故在中國的西南地區確實是有著該項種類。江蘇省婁縣志稱玉蜀黍曰雞頭粟。故在長江下游的平野中,可視為與田藝蘅的鄉里相同,亦具有很多紅鬚的品種。
田藝蘅尚附記一很重要的事項。他故鄉的錢塘江下游地方,是水田植稻的地帶,植麥甚少,故如玉蜀黍似的夏季作物,縱令傳入,其擴大裁培的可能性是很少的。故田氏故鄉的錢塘縣,鄰接於『飲食須知』作者賈銘的故鄉的海寧縣及李時珍家鄉的湖北蘄州等地的方志的物產項中,皆不見有玉蜀黍的記載。農作物中,裁培不多者,是像少量的藥草一樣,在方志中是不一定會被採錄的。
|
二、 |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有一大部分專記植物。『本草綱目』開始附有圖畫而記載玉蜀黍,謂玉蜀黍是由西土傳來。所謂西土,是被解為明代的西番,亦即是指青海地方。民間的傳聞,不一定十分正確,故以應解作泛指自甘肅至雲南的西藏高原的東麓。
迄今為止,一般以為玉蜀黍的傳入中國,是距『本草綱目』刊行的年代不遠**。但李時珍與田藝蘅,其著作的刊行,在其生前皆未完成。故玉蜀黍之見於中國,可推測其當遠在該項書籍(于按:指留青日扎與本草綱目)的出版年代之前。
這一觀點,自De Candolle起,至現代的萬國鼎、天野元之助為止,都是相同的。其前提是在哥侖布到達美洲以前,舊大陸上根本不知有該一作物。
據萬國鼎等,中國方志中記載玉蜀黍最早者是安徽省穎州志,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刊行**。這是與葡萄牙人始至廣州同年。吾們不能想像在該一年開始栽培的作物,立即記載於方志的物產部中,故其傳入在該一年代之前。萬國鼎推測謂顈州的栽培玉蜀黍,可能是在哥侖布發見美洲後不到十年的時期中。
于野元之助與筆者皆嘗調查日本內閣文庫的順治(1654)穎州志,在物產項皆未見有相當於玉蜀黍的作物,故未能確證萬國鼎之所云。但清初的方志,其內容很多並不繼承明代的方志。其顯著的例證,是大清一統志的編輯,完全沒有考慮大明一統志。再有,在水田植稻的地方,玉蜀黍是夏季的旱地作物,亦許古時雖嘗栽培,而後來卻已衰微。萬國鼎教授等在刊行中國農學遺產選集時,嘗調查全國的方志,故萬氏之言,似可信任。
如果萬氏的見解是正確的,則不能不考慮此項傳佈如何方纔是可能的。如果這一說明甚為困難,則De Candolle 儘管否定,吾人卻不能不推定在哥侖布以前的時代,亞洲已經有可能是有著玉蜀黍的一種。事實上,甚至在美國,亦有具有這一意見的學者**。
E. Anderson及其共同工作者,有此主張。
縱令玉蜀黍的發生地是在美大陸,而在哥侖布發見美洲以前,玉蜀黍的栽培已擴到美洲以外**,則不妨假定在哥侖布以前的某一時期,玉蜀黍已有一個品種傳達於舊大陸的某一角隅。其間並沒有什麼矛盾。例如丹麥的航海者、西伯利亞的某種族、或是Polynesia-Melanesia居民的活動,皆可能具有著媒介的性質。
據美國的研究者,在舊石器時代,嘗發見有玉蜀黍的花粉。據此推定在舊石器時代的人己嘗利用玉蜀黍。英國倫敦大學的學者,推測亞洲系的玉蜀黍是發源於緬甸北部附近,但似不決定以玉蜀黍的起源為在亞洲。關於這一點,是與Michigan大學的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者談話後確定的。參閱古野清人:原始文化扎記pp. 49~54,(1967)。
本草綱目的圖畫,據說是李時珍之子所繪。這圖決不能說很妙,故不能據以討論細微的部分。但一方參閱記載,可知所繪者確玉蜀黍無疑。記載曰「苗葉皆似蜀黍」「肥矮亦似薏苡」,圖中所繪者是葉間的節間很短,高是三、四尺,頂上抽出一花蕊,而並列著一有毛的穗**。穗上的子實是粗粒,而排列不整。柄長。其形態與蜀黍類似。這或許是為要將雌穗軸明白顯示起見將苞葉及葉的一部分除去後所繪的圖,看上去很奇怪的地方,都是波斯型玉蜀黍在形態上的特徵。
李時珍的記載,穗鬚是白色,故與田藝蘅所觀察的品種不同。「以火炙之,爆為白花」,這是指示著是糯的品種。糯的玉蜀黍,作為突變,各地皆有出現。但縱觀世界,作為糯的玉蜀黍的品種群,與其他穀類之糯的品種群,共同形成為地方的特色者,是限於雲南緬甸地區。故李氏的記錄,與其說是一種偶然,不如說大概是雲南緬甸的糯玉蜀黍的品種群已傳入李氏觀察範圍的長江流域,較為妥貼。(于按:雲南緬甸區域的的穀類的糯的品種,確是一項特色。該一區域的居民,是以糯米為食糧。玉蜀黍的糯的特性,英文符號所謂waxy者,是在該一區域首先發見的。)
李時珍父子所觀察的。可使人推測這似是沿著喜馬拉亞山系分佈的產於中國內陸深處的玉蜀黍(圖一)。

圖1:(左)植物名實圖考所載1848 。(右上)初版本草綱目1590。(右下)承應和刻本草綱目 1653
這一植物給人的全體的印象與N.N.Kuleshov所揭示的波斯型玉蜀黍的相照(圖二)甚為近似**。古今圖書集成亦採用本草綱目的這一個圖。故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似是異樣的形態,似可考慮:在當時卻真是表現著玉蜀黍的形狀。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maize. in H. Kihara (ed.),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29.
圖2:(左)Bokhara所產波斯型玉米。(右)N.N. Kuleshov, 1929 將左圖去葉後
但清朝後期的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中的圖,則與『本草綱目』中者不同,相當是寫實的,有旗葉,節間短,葉長,葉綠皺,苞葉將子實完全遮掩,其形態是作愛琴海型。這是在亞洲各地很普遍地可以看到的形態**。至少,在農學者方面,可以看出這與『本草綱目』所示者是不同系統的品種的寫生圖。
H. H. K
故明代散在中國本土的玉蜀黍與清代中期以後擴大栽培的玉蜀黍品種,很明顯地,其系統是不同的。至於近時的『五穀史話』,「玉米」中所示的圖,則皆為日本及中國沿海岸很普通的Caribbean Type的玉蜀黍。
|
三、 |
天野元之助氏嘗追蹤玉蜀黍栽培地區的展開過程,欲求闡明玉蜀黍在中國境內的傳佈途徑,其結果不一定可說是成功的**,在比較新近的歷史時代引入中國的作物,在各地方志中,其內容縱或不一定十分正確,但皆帶有說明,說是外來的。
天野元之助1962中國農業史研究。p. 53~58.
一般傳說是由於張騫傳入的西瓜葡萄,時代很古老,栽培很普遍,在方志中,大抵皆不載來源。但可視為與玉蜀黍同傳入的美洲大陸原產的作物如馬鈴薯、甘藷、落花生、煙草等。則在各地方志的物產部中,大抵皆附記其來源。試舉數例如下:
「淡芭菰」種出東洋。莖葉皆如秋菊而高大。邑人多植之,切為白絲,蜀中之名品也。稱曰白煙。(四川遂寧縣志,一七八七)。(于按:遂寧縣志文是據日文譯出,未及對照原文。)
「番藷」一名甘藷。根葉皆可食。其種有朱者,有白者,有皮肉俱紅者。明萬曆中得之呂宋國。凡沙礫之地亦皆可種,不甚費人工。(福建漳浦縣志卷二,1700)。(于按:漳浦縣志文,嘗覆按原文。是民國十七年翻印本,有康熙三九年序,原序年號作嘉靖。)「馬鈴薯」洋種傳來,亦合土宜。(福建建甌縣志一九二八)。(于按:嘗覆按原文。)「落花生」為南果第一。以其資於民用者最廣。宋元間與棉花、蕃瓜、紅薯之類同為粵估自海上諸國得其種歸種之。……落花生曰地豆。……今已遍于海濱諸省(檀萃,滇海虞衡志)(于按:嘗覆按原文。)
即在中國方志或其他記錄中,對於新來的作物,大抵皆傳述其由來。如玉蜀黍是由同樣方式傳入,則似應有同樣的記錄。但是,祗有玉蜀黍,在本草書中,是說來自西土或西番。這究應如何解釋?如籠統地說是因民眾沒有傳述正確的知識,似不能說是一謹嚴的解釋。要之,至少就玉蜀黍這一農作物言,在中國方志中,絕對沒有絲毫跡象說是由萄葡牙人自海道傳入。筆者不明白玉蜀黍之傳入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與葡萄牙人之東來聯結在一起?或一定要規定玉蜀黍是由哥侖布方引入舊大陸?如有明確的根據,布望讀者仍提供。
如果沒有根據,則在現在的常識上縱或是可笑的異說,似亦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玉蜀黍的乾燥種子,一個旅行者可攜至很遠的地方,故其栽培地很可能分散作點狀。至若某處的居民完全食用玉蜀黍,玉蜀黍形成為定居農耕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則大概是要相當長的期間。
例如Swingle謂中央細亞的回教徒在十六世紀中葉由麥加傳入新疆或西藏,而由此傳入中國本部(W.T. Swingle 1934 Maize in China. Nature, 133:420.)。關於這一見解,筆者是不同意的。
若作為珍奇植物之一而予以栽培,則其栽培是有限度的,縱或一時性地可成為特產,而要繼續發展成為產業是須要著各色各樣的條件。據此觀點,則在方志類中,止於一州一縣的小域時,在量方面,可說尚是不安定的。例如正德顈州志的記載,在後代的物產項中,是把玉蜀黍除去了的。如果不止於一府一縣,例如在各省的通志中,其栽培涉及於廣大區域者,則對於其開始記載的時期,應可視為在該一時期該一作物栽培已久、並已安定的證明。
中國的玉蜀黍這一正式的名稱,是由『本草綱目』而方為學術界所知道的名字。在『本草綱目』之前,是稱番麥,即以為麥的一種。或稱包粟、珍珠粟,而視為粟的一部分。此外尚有苞米、棒子、玉榴等俗名。至如觀音豆,雞豆粟的稱呼,則如無預備知識,實無法想像其所指者為玉蜀黍。但是根據該項名稱,要確定其為玉蜀黍,有時是有困難的。例如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引直省志書,把當時普遍的名稱玉麥、番麥,皆包括收錄在麥的項下**。
中國以蕎麥亦納入麥類中。故中國之所謂麥,大概是汎指磨粉後食用的穀類。中國人以前對於玉蜀黍大概亦是磨粉後食用,故亦稱曰麥。玉字大概是因其穀粒的光澤而來。雲南大姚縣志曰:「其用適與穀麥無異」。
至最近的中國農學遺產選集,則畢竟是不同了,不再誤以為麥。但『五穀史話』中所記中國各地方志中的有關玉蜀黍的名稱,究竟以什麼根據決定其為玉蜀黍,則不無若干疑問。例如被視為中國第二部最古的方志,是1531年刊行的嘉靖廣西通志(在日本內閣文庫中不是有此本),其中有語曰「稷俗名明禾」。『五穀史話』以為指玉蜀黍。其根據何在,並無說明。
在萬曆太平府志中有語曰「稻,太平之人名曰畬禾」。這是土人以稻(大概是旱稻)與普通的燒田(畬)作物相區別的名稱。廣西通志謂「稷曰明禾」者,大概是因土人本來種的是其他的雜穀,而新來明人將稷攜入,故稱明禾。這稷,按傳統的解釋,是指後人所說的粟(Setaria),據後人轉訛,是指高梁(Sorghum)。
其次,在臺灣出版的明代方志選中,有萬曆廣西通志。其中不見有相當於玉蜀黍這一作物的名稱。『五穀史話』究屬有何根據決定謂明嘉靖時在廣西已有玉蜀黍,其說殊不可解。同一皇朝的皇帝的交替,而重修一個地方的方志時,對於前代的方志,完全不加參考,大概是不可能的。
要之,在『五穀史話』中,檢討各地方志的物產的結果,在明代有玉蜀黍者,是有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江蘇、安徽、廣東、廣西、雲南等十省。在此處,有一點值得注意,即:玉蜀黍如果是由南海路線傳入,而在明代的浙江福建二省的方志中,卻不見提及玉蜀黍之名。但田藝蘅是浙江人,李時珍是湖北人,田李二氏已在其鄉里實在看到了玉蜀黍,故在明代末葉,不妨視為玉蜀黍已散佈於中國的全境。如謂玉蜀黍之傳入中國是在明末,並祇有南海一條路線,則在短期間內,其散佈會如是之廣,是不很容易使人理解的。
在另一方面,如欲根據地理分佈,以求知其傳佈的途徑,則根據方志的省別的分佈,不很容易進行研究。然如根據州縣的記錄,以推測栽培集中的程度,則或可據以推測玉蜀黍在某一區域的栽培時期的長短,即或可推測某一區域引入玉蜀黍的遲早。又如同一地方的方志,連續記載有玉蜀黍,則可推測其栽培量多,若在舊志中有而在新志中消失,則似可推測其栽培量減少,而已失去其重要性。據此原則,則在十六世紀中葉,已廣汎地栽培玉蜀黍的,有雲南省的大理、蒙化、永昌、鶴慶、姚安、景東等六府,即金沙、瀾滄、怒江三大河自西藏高原流出而將要分開時高原區域,似為集中栽培著玉蜀黍的場所。
上述區域之各地區中的詳細的分佈,則要到後代方纔明白。惟在該一區域的大部分的縣志州志中,皆記有玉蜀黍,其說明亦極為詳細,故似可推測玉蜀黍是很早已在該地普及的作物**。該一地區緊接於所謂西番之南,而是在西番與明代苦心討伐的金齒、平緬、芒巿等蠻族諸衛之間,故在中國本土言,是很容易與所謂西番相混淆的。
雲南許多縣志,對於玉蜀黍的說明極詳細。上述大姚縣志,對於作為食物的使用方法與栽培法,皆說明極詳。
西藏有諺語曰「有犁牛處不長玉蜀黍」**,真正的西番,例如青海,溫量指數不足,玉蜀黍的發育困難,故作為玉蜀黍傳入中國本部的傳佈基地,無基意義,是一如De Candolle之所指摘。
據中尾佐助教授的指示。
De Candolle是不承認玉蜀黍西番起源說的。事實上,在四川西部的藏族居住區,到清朝末期為止,玉蜀黍尚未傳入**。
四川松潘紀略(1873)記有栽培經過。
但是,湄公河上游原在人民的秤戛野人的區域,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方併入清室的領土,其染齒成黑色,面上亦塗顏色,而其人是以包穀,即以玉蜀黍為常食。稻及其他作食糧用的植物,栽培極少**。故吾人當可承認其很早已將玉蜀黍包攝於其農耕文化中。縱令說哥侖布自美洲將玉蜀黍攜歸舊大陸,再傳入廣東,試問是誰再將這種子傳入如此偏僻秘奧的地方?
漢軍:滇南新語,收錄於小方壼齋輿地叢書中。
上述栽培玉蜀黍的區域,不是西藏貿易所經由的道路,故由回教徒經由新疆而搬運的可能性極少。除開與緬甸北部的原住民作種子交換以外,該一區域的居民,大概沒有其他方法可獲得該一植物。因為在該一時期,以中國本土言,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尚有很多地方不見有玉蜀黍的栽培**。如上述推理是正確的,則該項野人栽培的玉蜀黍的品種,大概不會是由葡萄牙人東傳的Caribbean Type。關於這一點,今後的野外調查,大概是會證明的。
參閱湖廣通志、四川通志、福建通志。
|
四、 |
在雲南西部高地分佈甚密的玉蜀黍的栽培,究係始於何時,現尚不明。但栽培遍及於四萬平方公里的山地全境,其傳佈決不是一短促的時期。葡萄牙人到達印度西岸是在16世紀初葉,而中國文獻中有玉蜀黍出現,是在16世紀中期,這短短的50~60年會傳佈如是之廣,實很難想像。因就當時的玉蜀黍言,與稻及當地已有的旱田食糧作物競爭,玉蜀黍實在不能說是一豐產的作物。
關於這一點,稍後另當有說。但雲南栽培玉蜀黍,亦決不能說很古,故亦不能考慮其為玉蜀黍的原產地。例如樊綽的蠻書,關於雲南的農耕,記述頗詳,而沒有提到玉蜀黍,續雲南通志稿中記有原住民的方言,如稻、大麥、小麥、燕麥等主要穀類,是列記著夷族、泰族、白族、儸儸族等主要種族給予該項穀類的名稱。但對於玉蜀黍是祇舉示儸儸族、白族的Zhou-mo而其他種族皆無相當於玉蜀黍的名稱。這是指示著玉蜀黍的傳佈尚未普及於全部的原住民而似是一比較新的作物。
在記載明末清初的物產的直省志書中,玉麥之名是見於河北省清苑縣、山東省歷城縣、河南省昌邑縣、延津縣。在現在,玉麥之名,在雲南省,是限於西北部;在省城昆明,是稱包谷(包穀),這是由貴州擴展到雲南的名字(24)。其他如四川省西部,亦尚留有玉麥之名。據此以觀,玉麥之名,在中國,嘗廣佈於各地,而現在是殘留於偏僻的地區。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64漢語方言詞匯。
在清初,有玉麥的地方,現在是稱棒子或包穀,這是指示著後代的新的名字壓迫著舊名玉麥,而使之趨於消失。又如江南地區通稱的番麥,現在袛是殘留於福建廈門、同安,而江南卻是用俞賣(于按:當是玉麥的寫音)棒頭等新的名字**,此項方言變動的原因之一,或可考慮是因新品種出現,代替了舊的品種,因此聯帶著使舊的名稱消失。例如雲南本來的舊品種的玉麥,因有稱曰包穀的豐產的新品種自貴州進入昆明,與昆明之西的玉麥區域楚雄接觸,其結果,在楚雄地區是產生了新的名稱曰包麥。十九世紀末期雲南地區有關玉蜀黍的方言的分佈是如第三圖所示。
湯起麟,玉米p.1,列示苞蘿、六谷、玉茭等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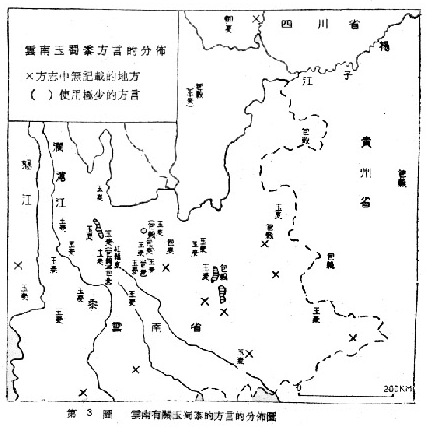
在道光二十五年(1843)的姚縣志中,並舉玉麥與包穀,而列述二者之異曰:「包穀即玉蜀黍,一名玉高梁。其狀,莖如甘蔗,高七八尺,每節葉間出一苞」。「玉麥似甘蔗而矮,每株二三苞不等」。南寧縣志引道光十五年(1835)的雲南通志稿曰「大麥小麥燕麥三種植於陸地;玉麥植於園中,似蘆而矮」。據是則所謂包穀與玉麥,似是在高度上有著差別,即包穀高而玉麥矮。就野外觀察的觀點言,似可推測這是Caribbean Type 與Persian Type之異,而大概在產量上亦有著差別**。
Caribbean Type玉蜀黍的典型,見於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這可視為葡萄牙人自Caribbean sea攜來的系統。
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績雲南通志稿中,有很值得注意的記載。其言曰:「謹按,玉麥形似包穀,惟其苞大而子實小,不成行列。」據此以觀,可說:稱曰玉麥的玉蜀黍系統與子實排成行列的Caribbean系統。在系統上顯然有別,又玉麥的粒色有藍紅等,且多糯的品種;而屬於包穀的系統,其子實有黃紫瑪瑙等色,而大多是硬質,或似齒粒種**。
湯起麟,玉米,p.2。
子實小而排列不整齊的玉麥,每株的苞數少,故其產量大約不高。至稱曰包穀的新品種,是由東南進入,每一節葉間有苞,自高度以觀,可推測其為Caribbean Type**,其產量高,故似很快就普及於各地。此項推測,將來的實地調查,將可證實。儘可能的文獻的研究,當可在作實地調查前,先建立一項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
大姚縣志曰:「每節間出一包,如冬筍。綠籜數重裹之。籜似竹而軟,中有胎,如茭筍,根大而末銳,其格如之房子,格中居然有蛹土在,平鋪密綴,如編珠然,初含漿,漸實漸老,或黃或白或紫或赤,五色相鮮,籜顛吐鬚,如絲如髮,色紫而絳。每莖或四五苞,或二三苞。莖頂有穗。正似薏苡。」據是以觀,可知稱曰包穀的系統,決不是如『本草綱目』所示玉蜀黍之于實裸出的系統,並與玉麥似的子實不成行列者亦不同。(于按:本節中所引方志文,皆係自日文譯出,不獲與原文對照。)
|
五、 |
上云,要根據文獻先作準備的研究,但在日本可利用的文獻,與中國本土比較,在數量上是很有限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把握問題,作有效的整理,俾使用在日本可獲得的資料,亦可作某一程度的研究。這樣的問題,可舉示者有三:
一般相信的由葡萄牙船攜來的新大陸原產的農作物,其由葡萄牙船攜帶的確實性如何?
調查在日本可獲得的中國方志及文學書等,檢討明代文獻中所載的玉蜀黍的名稱形態,並追溯記載的年代。
主要的是根據方志以追溯新大陸原產的農作物在中國境內的傳佈途徑及其年代。
研究的目的是玉蜀黍,但玉蜀黍是新大陸原產的許多農作物之一,此外尚有煙草、甘藷、落花生、馬鈴薯等,亦皆為美洲原產的農作物,這大約是在同一時代自海外傳至亞洲,傳入中國,故對於玉蜀黍,似不應視單獨傳佈的植物。在亞洲,玉蜀黍是由於外來文化刺激所一形成的複合食物文化的要素之一,這似應與同類型的作物群包括在一起,而一同考慮其傳佈。質言之,吾人對於玉蜀黍的傳入中國,是應視為一種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或應視為文化複合之地域的形成的一項地理學的問題,而加以處理**。
藪內芳彥、飯沼二郎譯,Emil Velt著:農業文化的起源(1967)。
關於上列三項研究題目,就第三項言,筆者的研究,尚不及一半,其報告當俟諸異日。現將就第一及第二項,敘述筆者考察所得,以就正於方家。
關於第一項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日本的研究者,在常識上,美洲原產的作物,由南蠻傳入的印象,皆很深刻。故對於種子、島銃(于按:即步槍或手槍)、煙草、基督教、紗布等複合文化的內容,皆有一種先入之見,以為當然是由葡萄牙船傳入日本。關於這一點,實在有對於史料作詳細檢討的必要。就中國言,大概亦是同樣的情形。關於中國人(漢民族)本身的意識,外國人很難作深入的探討。就文化複合問題言,往往有以一推十的傾向,這一點,在研究者似是不可不戒慎的。
試舉實例。甘藷、煙草是經由九州平戶傳入日本**,在日本首先栽培甘藷者是英國的領事館員,但日本人遺忘,而往往以為是與洋槍一同由葡萄牙人傳入。但這是因日本與海外諸國的接觸大多是平穩的情形下進行的結果。日本人往往以為中國人與外國的接觸亦是同樣的情形。筆者在此處要特別指出,事實上不是如是。
參閱村上直次郎編:異國叢書(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的平戶;宮本常一,甘藷的歷史)。
矢野仁一對於明代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有極詳細的研究**,據是則明代中國與葡萄牙的交涉,絕非平穩(于按:至今遺留的創痕,是澳門),在此期間,很平凡的農作物如玉蜀黍與落花生,是不是會傳佈,實為疑問。就與中國的接觸是不是平穩言,葡萄牙人與後代的大西洋人(意大利人)是不同的。現在根據矢野仁一的考證,先略述葡萄牙人與中國接觸的經過的大要。
矢野仁一 1928中國近代外國關係研究。
葡萄牙王於1508年令人探視麻六甲,其使節為麻六甲王所抑留,葡萄牙遂於1511年攻佔麻六甲。1514年,即明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始出現於中國,進行著商品交易。交易的場所不明,矢野推測以為商品是積載在南洋船或中國船上,而葡萄牙人祇是以乘船人員的一部分的身份東來。
農作物,並且是極平凡的食用品,大概不會被攜帶作為交易用的商品。南洋船或中國船上的船客的葡萄牙人,如祇是積載著交易用的貨物,則大概不可能以其食用作物傳佈於交易對手的國家的農民。據葡萄牙人的文獻**,中國是禁止其人民出至海外,故居住於麻六甲與南洋各地的漢人(即華僑)各皆自稱為居民住地的王的使臣,而往來於中國及其居住地之間。
Gaspar Da Cruz:Tractado da China,據藤田豐八轉引。
實際上,這樣的外國籍的漢人,大約為數不少**。如葡萄牙人所雇用的,是這樣的中國船,其食糧流入於中國農民之手,而被用作種子的機會,大概極為稀少。
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四。據矢野氏轉引。
葡萄牙船直接到達中國,大家熟知者是正德十二年(1517)。據籌海圖編,佛郎機人(于按:其時稱葡萄牙人日佛郎機人,稱荷蘭人曰紅毛人)是到達廣東懷遠驛。又據萬曆三十年(1597)的廣東通志,「佛郎機本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駛大舶直入廣州灣,以進貢物為名,發射大砲。中國官吏,以如此進貢,無前例,止其行。彼等止於東莞縣之南頭,設住居,圍柵警戒而生活」(于按:廣東通志文,是據日文譯出,未覆按原文)。明實錄,明史的記載大體相類。
此時,吾人在考慮農作物的傳佈上,要注意的,是:佛郎機即葡萄牙人是假借著進貢的名義。在他們,是隨著歐洲人的習慣,大概以為如是則在通商的交涉上比較有利。但明庭的習慣,則對於正式的國家使節,是禁止著其作私船的貿易。故葡萄牙人縱令在船上裝載其本國或南洋的產物,一方進行其官式的交涉,一方經營走私的貿易,在其要保持官方使節的名義下,其走私貿易,應當是受著很大的限制。
如矢野氏之推測,佛郎機人在被抑留的數年間,可能是以其一部分商品進行著走私貿易,但當然是秘密行為,故其商品內容,當係限於少量而高價的貨物,如落花生或玉蜀黍之類,其買賣或交換的可能性,大概是極少的。
並且,再有一點須要注意:即該項新大陸原產的食糧用農作物,在其時的葡萄牙,大概產量亦不會多,縱令在航海時,有一部分玉蜀黍被用作食糧,大概亦祇會裝載於葡萄牙人自己的船隻,而不知道該項農作物的南洋船或中國船,大概是不會加以利用的。故從作為貨物的價值看,從與中國農民的接觸機會看,葡萄牙人直接將玉蜀黍傳佈於中國本土的可能性,決不會多。
從上述觀點看,嗜好品的煙草,其情形或稍有不同。煙草是有著被利用為交易物品而很迅速地傳佈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廣東省內煙草栽培之發達是在清代中期以後,並且,由福建湖北方面傳入之說,甚為有力**,這就是說,像煙草似的強有力的農作物,航行至廣州的葡萄牙船,在傳佈上,亦未見有顯著的作用。
光緒廣州府志謂「煙草來自南雄湖北方面,為廣東本來所無」。道光南雄州志謂(1753)「舊志未載」,故以為廣東栽培煙草是不久之事。江西省方面,廣信府志瑞金縣志謂煙草來自福建。(于按:上列方志,皆未及檢視原文)。
此處要注意的,是葡萄牙之向廣州的正使Tome Pyres一隊的影響,實在說,是不如其向福建漳州的福使George Mascarenia的船隊者之大。這是因Pyres一隊在廣州被抑留二年,以後雖獲到達北京,而其後到達的Simon de Andrade發揮了各大種暴行,故受著中國人的排斥,嘉靖二年(1522),在廣東省,經過戰鬥,葡萄牙人完全被趕出廣東。換言之,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在廣東的初期的接觸,決不是和平的,而很顯著地是敵對著的。故縱或有農產物的交易,其效果決不會大至可對於後世發生影響。
惟在漳州的葡萄牙船與中國居民的接觸,卻不像在廣州似地是戰鬥性的,而比較和平。福建省同安縣人林希元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與翁見遇別駕書」曰:
佛郎機之來,皆以其他之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沈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最平。其日用飲食,皆資於吾民。米麵豬雞之類,價倍於常,故邊民皆樂與為巿。迄未侵我邊疆,殺戮人民,劫略財物**。(于按:爻布元信是由日文譯出,未獲覆按原文)。
藤田豐八1918 葡萄牙人到佔據澳門為止的許多問題,東洋學報8(1).
這似可視為和平通商。後代的漳州,作為中國的煙草產地,嘗為一方之雄(36)。
晉江縣志(1765)謂「土煙不如漳」,龍溪縣志曰(1762):「惟漳煙稱最」。
又林希元家鄉同安縣的鄰縣安溪縣的縣志,在福建省現存的方志中,是比較上很早記載著玉蜀黍的方志**。故葡萄牙航向中國傳入農作物的可能性,或可考慮漳州的路線。葡萄牙人在被廣東逐出以後,時間及理由,皆不甚明瞭,是在浙江寧波府出現,在稱曰雙嶼的島上經營貿易。
安溪縣志(1757)曰:御米一名番麥,穗生節間。
藤田豐八**推測曰:葡萄牙人大概是因日本人在寧波與明人貿易甚盛,故可能是以雙嶼為轉接地點,而進行著與日本的貿易。但葡萄牙人在雙嶼的和平貿易,亦不能長久維持,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仍被驅逐。此處,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與寧波府接近的杭州府,在萬曆七年(1583),已有落花生存在。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當時的大部分的中國官吏,對於葡萄牙人皆甚厭惡,甚至有人說:與其他國家的船可以交易,而對於葡萄牙船,則無論如何,一定要加以排斥**。
據藤田所引文敏公全集卷十下「兩廣事宜」文。
其理由,有若干事件可以考慮,而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是:Simon de Andrade的暴行。傳說:葡萄牙收買中國嬰孩而加以殺害,故對於佛郎機抱有好感的爻希元亦曰:
佛郎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而收買子女,不能謂為無罪。推其罪尚不至於強盜。最可惡者,為掠取邊民,以行買賣。總之,葡萄牙人賤視亞洲人民,以之為奴隸而肆行買賣,大概是被當時的中國人厭惡的最大的原因。
葡萄牙人的交易方式,據在廣東省負警備責任而強硬主張排斥佛郎機的朱紈的「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是如下所述。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佛郎機人)駕船在海,以胡椒銀子換米布紬緞,以為買賣,往來於日本漳州寧之間。……在雙嶼,有不知名客人,操小南船,載麵一石,送入番船。謂有綿布、綿紬、湖絲,編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幸又寧波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銀百兩謂買緞子、綿布、綿紬……
這是說,佛郎機人以銀購入中國工藝品,或是運入南洋的物產,以賣於中國居民,而購入當地所產的糧食。在這樣的交易方式下,似很難期待葡萄牙船會運來農產種子,以推廣於中國居民之間。並且葡萄牙人的貿易,大多是船在海上,進行著商品的授受,故似可曰:葡萄牙人並沒有在陸上定居,以試行植物的栽培。
1554年以降,佛郎機貿易,獲得中國官方的准許,葡萄牙人居住於澳門,以後的通商關係,比較平穩,但葡萄人的居住,自成群落,皆密集於巿街,而極少園地或耕地。這一點,從最初在廣州被拘留時代起,一直到後代為止,似無變化。據龐尚鵬疏,是說:(佛郎機人)近頃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幾已達千區以上。
其密集居住的形狀,可以想見。俞大猶書亦記其未獲准許而強行居住的狀態曰:商夷以強梗之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
萬曆廣東通志記其佔居狀態曰**:
托言舟觸風濤,願借蠔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茅舍。商人牟利者漸運瓴甓榱桷為屋。佛郎機人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為所據。蕃人之入據澳,自汪柏始。至萬曆二年建閘於蓮花莖,設官守之,而蕃夷之來日益眾。(于按:本文是據澳門紀略上卷修正)。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及所引文獻。
據此可知葡萄牙人佔居中國的土地,是過著與當地居民隔離的生活。故葡萄牙人在澳門雖是過著陸上生活,其傳佈農產物的機會,亦顯然受著限制。事實上,在澳門所在地的香山縣及其附近地區的方志中,到清朝末期為止,未見有新大陸原產作物的記載**。
道光香山縣志(1827)舉有和蘭豆、粟米(是指玉蜀黍)、甘藷、落花生,關於和蘭豆,記曰:近數十年來自澳門獲得種子。其他皆未詳記由來。祇是說:甘藷得自諸番,和蘭藷來自外國。所謂和蘭藷很可能是指今謂馬鈴薯。和蘭豆(菜豆),在福建漳州方面,乾隆初年(1740年代)己載於方志,故經由澳門的傳佈,是遠在其後。
|
六、 |
如上所述,根據方志的記載,玉蜀黍之廣大的栽培區域,是以雲南省西部的大理府為中心而展開。這是明萬曆初年(1576)的事情。如以該項栽培的種子為嘉靖三十三年(1554)初獲准居留於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傳佈,則以廣東與雲南相隔之遠,加以當時交通之不便,在時間上實太嫌侷促,而不能無疑。
在比較更早的時期,有沒有文獻指示出雲南是栽培著玉蜀黍?雲南方志的編輯,是以明萬曆年間者為最早。故據雲南的方志,很難再向前溯。但在本草書及遊記中,或可求取更早的記錄。至此,最先受到注目的,是『徐霞客遊記』,徐氏在萬曆天啟崇禎間遊覽中國中南部的山地名勝,而遺有詳細的觀察記錄**。徐氏足跡遍及廣西雲南,且遠至緬甸境界。故對於其記載,殊有詳加檢討的必要。筆者嘗詳檢香港廣智局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版本的『徐霞客遊記』,皆不見有有關玉麥或類似名稱的作物的記載。
徐宏祖:徐霞客遊記(于:版本從略)
所謂遊記或文學書類,往往有當地人視為日常普通的事象,不成為記錄對象,而在外來遊客,卻視為新鮮而予以記錄的。故遊記類有時可成為極有用的資料。但徐氏在雲南的大部分的旅行,是在冬季。這大概是這一位很精密的觀察者對於該一地域的特殊的農作物所以未有認識的原因,因此,依仗遊記類的收穫,碰運氣的機會很大,在目前,希望不多。
其次是本草書。本草書當然是記載當地的植物、動物與礦物,就一般而言,是記載植物的數目較多。中國的本草書,其記載的植物,是以華北、華南平野丘陵者為多**。至住在雲南而且直接觀察記載雲南當地植物的本草家,實在甚為稀少。
本草書中首先記載玉蜀黍者是李時珍『本草綱目』。但近於是同一時代或比較稍早的本草書,在日本有陳嘉謨著的『圖像本草蒙筌』(嘉靖乙丑,1565)及李中立著的『本草原始』(出版年月不明)。二者皆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在前者記有御米。據其記載內容,是指Amaranthus(莧菜屬)的一種。這是今後應當注意的植物。(于按:關於這一植物,千葉氏在另一文中有說明)。
但甚為幸運,在雲南圖書館彙集的雲南叢書子部中,收錄有蘭茂的『滇南本草』。蘭茂是明初洪武三十年(1396)生於雲南省雲南府嵩明州,是當時的學者詩人,其學問上的活動,是在正統年間(1425~49),成化十二年(1476)歿,八十歲**。
于乃義、于蘭馥 1957滇南本草的考證與初步評價。醫學史與保健組織,第1號。二氏謂據需南方志十種的引證,則蘭茂是承受著未周濂溪的學派,通醫學、陰陽道、地理、畫論,長於詩文,著述頗多,有韻略易通、聲律發蒙、性天風月通玄記、滇南本草、醫門要、玄壼集等。又務本堂本卷一往往有先生云云之語,故似夾雜著蘭茂弟子之文。蘭茂去世後,該地常遭兵燹,舊著多散佚。故蘭茂親筆的著作無遺留者,其居屋不復存留,亦無子孫(據嵩明州志)。
在『滇南本草』中卷,有「玉麥鬚」的記載,謂「焙乾可治女人乳腫」**。據筆者所知,這是有關中國玉蜀黍的最古的記載,而該項記載的時期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1492)以前。故該項記載如果是確實的,則玉蜀黍之傳播於中國是始於葡萄牙船之東航或非在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後不可之說,自將雲消霧散。
原文如下(雲南叢書本):玉麥鬚味甜,性微溫。入陽明胃經寬腸下氣。治婦人乳結紅腫,或小兒吹著,或睡臥壓著,乳汁不通,疼痛怕冷,發熱頭疼,體困 。新鮮焙干,不拘多少,引點酒服。(于按:參閱圖四)
但中國古代的文獻,往往有後代的增補或摻雜,故為要證明『滇南本草』的真實性,一定先要經由嚴格的書誌學的考證,證明『滇南本草』確實是蘭茂的著作,而有關玉麥鬚的記載,確實是出於蘭茂之筆,而不是由於後人的追加。這一工作,需要很高深的專門知識,非淺學的筆者所能勝任,但在目前,則祇能盡筆者所能,試為考查,尚待識者的指正。
『滇南本草』,至少是有兩個系統,而各有新舊的版本。關於這一點,試先看雲南叢書所收版本的解題者趙藩的見解。趙藩曰:
曩聞之先君曰:相傳輯雲南藥品者有三家:一沐國公琮,曰苴蘭本草;一蘭茂,一楊慎,皆曰滇南本草。沐楊惟傳鈔本。蘭有舊坊刻本,其中有劉乾添註數條。劉不詳何時何地人,死非蘭氏手定矣。至新坊刻蘭本,則太揉雜,且書中時稱止庵先生,決為無識者竄亂止庵之書矣。惟道光中皖人孫兆蕙以同知官滇,其人習醫工繪,得楊慎傳鈔本,蘭茂舊坊刻本,乃合校而彙編之,凡得藥四百一十種,分載蘭楊之說,亦間附已說,自繪為圖而刊之,曰一隅本草。其書尚可備醫家之用云。劍川趙藩撰。
上文是民國三年(1913)版(于按即雲南叢書版)刊行時的解說(序言)。關於這解說,在1957年,雲南圖書館參考部組長于乃義氏提出若干訂正的意見**。據是則沐琮不是在醫藥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的人,楊慎祇是陳述雲南的動植物,作為本草書的記載,殊不足觀。
于乃義、于蘭馥 1957滇南本草的考證與初步評價。醫學史與保健組織,第1號。
又孫兆蕙不是安徽人而是江蘇人,至所謂「一隅本草」則遍查雲南和地,不見此書。要之,于氏指出趙藩的解題文錯誤頗多。但于氏極反對「滇南本草非蘭茂作而為後人假托蘭先生之名所作」之說,又對於玉麥鬚野煙的記載為後代附加說,亦加以反駁。下文將引用于氏之說,以考察『滇南本草』究屬是怎樣的一本書。
在光緒昆明縣志中,謂「滇南本草,舊傳蘭茂作而序文作崇禎甲戍(1634),故非正統年間蘭氏之作」。道光雲南通志,亦記有同樣的意見。雲南藥物改進所編的『滇南本草圖譜』(1943),亦以為『滇南本草』記有應為哥倫布攜歸的玉麥與野煙**,故應是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後的著作。以上所列,都是對於蘭茂滇南本草成立的年代表示疑問的。
『滇南本草圖譜』一書,筆者未獲親見。大概該書未嘗傳入日本。試據雲南叢書本滇南本草,揭示其原文(于按:參閱圖五)務本堂本者後文舉示。二于氏以為此文所指者不是現在所說的煙草(Nicotiana tabacum)。現在所說的煙草是栽培種。所謂野煙,是指與煙草不同的植物。並謂在現在的雲南地方,應尚有相當於該一藥草的植物。據筆者所知,在煙草傳入中國以前,福建已有稱曰煙草的植物,例如康熙平和縣志(1719)曰:「煙草長僅及寸,細如絲,可收油燈之煙。今人以小盤植之,置案頭。一名虎鬚菖蒲。」大概是像石菖似的植物。野煙,或是指與此形似的野生植物。
但清時『植物名實圖考』的作者吳其璿,對於該項疑問,有一很明白的答覆。『植物名實圖考』記有相當多的雲南的植物,吳氏因此校對過『滇南本草』的相當多的不同的版本,而發見有記有「正統元年」的識語的版本。吳氏以之與雲南通志稿所引用的滇南本草對照,見文章及內容大不相同,故謂雲南通志稿所引用者大概是經後人增補,而有正統元年識語者則是蘭茂的原本**。
于乃義、于蘭馥:前引文。
筆者在上文謂『滇南本草』可區別為兩個系統,是據此而說。雲南通志稿引用,而吳其璿指出有後人增補者,就是趙藩解題中所云坊間的新刻本。這新刻本是光緒十三年(1887)昆明務本堂所刻印。卷一分上下。卷一上有圖。卷一下及卷二卷三皆無圖。無圖部分的內容,大體上與坊間的舊刻本相同,而記載順序稍有變更。共記藥品458種,其中有13種為重出。務本堂本的名稱是滇南本草,蘭茂的序無年號。又附刻有蘭茂著的醫門要上下卷。下文暫稱這版本曰務本堂本**。
筆者是參照著大阪武田株式會社杏雨書屋藏本。
吳其璿所云有正統元年識語的版本,吾人推定其大體上是蘭茂的原著,因為這是趙藩解題所云舊坊刻本。計有三卷。這被視為版本之一,而收錄於民國三年(1914)雲南圖書館編的雲南叢書的子部。但這一版本無吳氏所見版本的正統元年的識語,祇有本文,無圖。又葛根、商陸、紫蘇……等36種,無本文,而祇註有處方。藥品總數為280種,大半是草。對於這一系統的滇南本草,在這篇文字中是略稱曰叢書本**。
愛知大學圖書館藏本。
務本堂本與叢書本的顥著的差異,是:第一,務本堂本卷一上有圖,而此一上中所記的植物,幾皆不見於叢書本。務本堂本卷一上最後有落花參,據圖及記載,很明顥地可看出是落花生:故可指出這一部分是落花生進入雲南以後所寫成。
其次,務本堂本卷一上對於植物的記載法,與卷二、卷三者不同,其先記載者是各種植物的產狀與形態。在中世紀時代,祇是列舉藥品的味性藥效,是本草學方式的記載,而務本堂本卷一上者是植物學方式的記載,這在記載方式上是一項很重大的轉變。故對於務本堂本卷一上可以看出是接受歐洲科學影響後所寫成。
叢書本則明顯地是保持著古時的方式,是順次記載著味、性、藥效、主治,而完全不提到植物的產狀與形態。大概是因務本堂本的記載方式較為新熲顈,故近代編輯的『雲南通志稿』、『植物名實圖考』大多是引用務本堂本,尤其是大多引用卷一上的部分,這可說是當然的**。
雲南通志稿自滇南本草引用68種,其中有63種是自務本堂本卷一上引用。植物名實圖考自滇南本草引用53種,而文字已經增減,故那一部分是引用的,並不清晰。
在于乃義的考證中,因科學性及有益性亦以務本堂本為『滇南本草』的主流,就其所取立場言,亦可說是當然的。然自歷史的觀點以視滇南本草的兩個系統,則似可推測:叢書本是繼承著蘭茂原著的形態;迨經後人增補,至清初乃取新的記載方式,並重行編輯,其結果乃成為務本堂本。這務本堂本或許就是相當於趙藩所記的一隅本草。
|
七、 |
蘭茂,據傳是生於明初,而承受宋學系統的閩派的教育,故其所著本草書,當繼承著中古時代的本草書的系統。雲南叢本的滇南本草與務本堂者亙及全書的明瞭的差別,是:前者在藥品名後,先記其味,次記其性;而後者是先舉其性,後述其味。即記載內容的順序不同。試以之與古本草書的體栽對照,則雲南叢書本的滇南本草的形式,與本草經、名醫別錄者相同;而務本堂本與古本草書完全不同。
筆者以為蘭茂是忠於傳統的人,故不能承認務本堂本是蘭茂的原著。
雲南叢書本滇南本草與務本堂本滇南本草之有關野煙的記載,是如下所示:
雲南叢書本(參閱圖五)
務本堂本
野煙一名煙草(目錄中作一名小菸草)
性溫味辛麻,有大毒,治熱毒、疔瘡、癱疽、搭背無名腫毒、一切熱毒瘡,或吃牛馬驢騾死肉,中此惡毒,惟用此可救。
補註:吃此藥後令人煩亂不省人事,發迷一二時後出汗方省,不必著驚。蓋此藥性之惡熱也。
附案:一人生搭背,日久不潰將死,名醫診視皆言死症俱不下藥。後一人授此草,瘡潰調治全癒,後人因名:氣死名醫草。以單劑為末,酒合為丸者名:青龍丸。
試比較二文,可知本文是祇有味、性、主治,而其餘很明顯地皆為後代的補記或附註。此項補記或附註,大概是後人傳寫利用時,據本身的經驗而添入,以後乃遂混入於本文中。
野煙下註曰一名菸草,是後代誤以為Nicotiana煙草的原因。其原形似當為「小草」或「小菸草」。因在藥效部分記有對於動物蛋白的腐敗中毒是有效的。而Nicotiana煙草對此病症應當是無甚效果的。據雲南醫師蘇采臣之說**:在雲南地方實際上是有稱曰野煙的藥草,具有著滇南本草所記的藥效。這與Nicotiana煙草是不同的。
務本堂本滇南本草,在白花地丁項有註曰:性味前人無註治痔瘡生管。雲南叢書本,無右線部分。據是可知缺這一部分的雲南叢書本是出於務本堂本所云「前人」之筆。同時,務本堂本云性味,故務本堂本的校訂者就按此順序而修改。務本堂本所刻蘭茂的序文無年號,故是不是蘭茂原文,殊為可疑。序中有「余酷好本草,考其性味」之語,以後的校訂者,很可能是據此而先記性,後記味,但這是根據字面的解釋。一般的本草書,其記錄方式,都是先以口嚐其味,而後知其藥性。在蘭茂的序文中亦曰:「神農氏嘗百草而知藥性」。普通寫「味性」時,很可能誤以味為動詞,故寫作「性味」,但以前的本草書,其記載並不依照性味的順序。
在註的文字中,可注意的,是務本堂本改雲南叢書本的食為喫,改發暈走動為煩亂,改發背為搭背,改出頭為潰。就註及附案的文體以言,務本堂本似是比較接近於清代的近似口語的文體。改食為喫或吃,是其顯著的例證。務本堂本,這傾向,甚為顯著。例如雲南叢書本作三日五日,務本堂本改為三天五天,又改煎食效為煨吃好等,都是例證**。
出於中國語學教授鈴木擇郎的指示。
要之,註、案、方等皆為後人所附加,而可視為碩學蘭茂的原著的部分,是祇限於記載味、性、主治的本文。故雲南叢書本在形態上是保持著古代的表現方式,而務本堂本,則根據形式,可推測是在明末清初時改寫。
例如雲南叢書本滇南本草的土茯苓項曰:(參閱圖六)

這似是菌的一種。其本文是到五淋赤白濁為止,大概是治泌尿器病的。其下文說婦人紅崩白帶,附註有藥的處方,這可視為由後人附加。文中又說到楊梅瘡,這就是梅毒,這當然是哥倫發見美洲以後的疾病**。故對於該項記載可視為以後混入於本文。務本堂本將上項內容,分項列寫,這頗有助於筆者的推測。
據E. H. Ackerknecht, M. D.? 1965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 及H. Zinsser 1934 Rats, Lice and History。梅毒,並無確實的根據可說是由哥倫布航海至美洲後攜歸;但在1500年以前,亦無明白的根據說可說舊大陸方面確有類似這一症狀的疾病。故東方之有這一疾病,故東方之有這一疾病,應當說是在葡萄牙船出現以後。
務本堂本土茯苓項曰:
土茯苓 一名次飯團
子名遺仙糧
性平,味苦微澀,治五淋、白濁,兼治楊梅、瘡毒。附方治婦人紅崩白帶。
土茯苓水煨引用紅沙糖,治紅崩。白沙糖治白帶。又方治楊梅、瘡毒。
土茯苓或一兩或五錢,水酒濃煎服。
又方治大毒瘡、紅腫未成即濫。
土茯苓為細末好醋調數。
補註:子名仙遺糧,治楊梅、結毒、丹流等。
「婦人紅崩」下有處方,楊梅結毒是兼治,皆不能視為原有的記載,據是則對於雲南叢書本的土茯苓項可視為將本文及附加部分一貫地列記著,因此遂引致混亂。
據是判斷,則吾人所重視的對象,即玉麥鬚項的記載,似極少後人附加的跡象。雲南叢書本的記載是:
玉麥鬚 味甜,性微溫,入陽明胃經寬腸下氣。治婦人乳紅腫,或小兒吹著,或腄臥壓著,乳汁不通,疼痛怕發熱,頭疼體困。
新鮮焙干,不拘多少,引點酒服。
務本堂本是將性味顛倒,又誤入為人,乳汁不通下作體紅腫,怕冷作冷,頭疼作頭痛。此外無甚差異。在處方處,焙干作焙乾,作點水酒服。此中,處方是後人附加,可除去。如是則在內容上叢書本與務本堂本大體相同,都是記載著作為藥品的玉蜀黍的花柱,毫不足異。自玉蜀黍的花柱中可分離出Flavone的配糖體(glycoside)的Isoqueucitrin,在現在亦利用以為利尿劑**。
據迆田桂太編,增補改訂資源植物辭典(一九五七)玉蜀黍項。
這是說,其作用可促進內分泌機能。在當時,大概以為在促進乳腺的分泌上亦有效果。
叢書本滇南本草,包括野煙在內,共記載280種藥品,現在已知野煙不是Nicotiana煙草,楊梅瘡云云是後人補註,而玉麥鬚一項,在雲南叢書本與務本堂本中,其記載的形式與內容皆無異處,故至少在筆者,認為毫無根據可視為出於後人的附加。
為鄭重起見,試再檢討務本堂本卷一上的落花參的記載,有關卷一上的記載,最先要注意的是與卷二卷三者不同,是祇記味而不述其性。根據這一點,即可判斷務本堂本滇南本草卷一上是與一般的本草書以及同書的卷二卷三不同,是一種後代的方式。務本堂本卷一上的落花參項曰:
落花參 味甘熱無毒,鹽水煮食,治肺癆。生用水瀉炒,用燥火行血,治一切腹內冷。
積肚疼服之即效。枝葉治鐵打損傷敷處。小兒不宜多食,生食變為疳積,忌之。
所謂即效、跌打等語法,都是新的語調,似非出於蘭茂的原著。此種表現,在務本堂本卷一上中是一通同的方式。在卷一上中隨處可見有神效、其效如神等。但在雲南叢書本與和雲南叢書本接折的務本堂本卷二卷三中,完全不見有此種語法,要之,務本堂本滇南本草卷一上,其內容有落花生、楊梅瘡的記載,而全部記載的方式具有一貫性,其物品皆為中國人所初見,故可以判斷這是哥倫布以後的人航行至東方以後,由蘭茂以後的所附加。
至如雲南叢書本的滇南本草,則除開後人的附註及處方外,其藥品的排列順序,與務本堂本者亦頗有出入,吾人縱或可疑其非完全為原形,但關於藥品本身,當可考慮其是保持著蘭茂所的原形。吳其濬大概亦嘗考慮這一問題,『植物名實圖考』所引用的『滇南本草』的文字,是與後出的雲南叢書本者相同,先記其味,次記其性**。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1848)中華書局1963年版。
要之,在目前,經書誌學(版本學)的檢討,『滇南本草』應被視為深通明代初期的語言學醫學及其他學問的蘭茂的原作,在後代嘗有人加以補註。惟補註的部分,根據用字文體,大體皆可加以檢定區別。至有關藥品的味、性、主治症狀的本文,則視為出於蘭茂本人的記載,當不至有誤。故其記載項目之一的玉麥鬚,如無明白的證據可證明其為由他人補入,則吾們應當承認在蘭茂的時代,即15世紀中葉,在雲南的一部分地方,確已有玉麥存在。換言之,對於滇南本草中的玉麥鬚,應當視以為有關玉蜀黍的一個系統的記載。
如視此一項後代所附加,則一般以為比較容易傳佈的新大陸的其他作物,例如煙草落花生等,應當是同一時代的產物,而皆不見於蘭茂的著作中,這是一很大的疑問。關於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似亦可作同樣的考慮。如玉蜀黍是由葡萄牙人所傳入,則理應尚有大約是同時期傳入的其他的作物;而本草綱目所記載者卻祇有番麥。
李時珍廣羅全中國的藥物,加以記載,何以會不見煙草與落花生,實在很難說明。唯一的說明,是:玉蜀黍是經由稱曰西番的地區傳入中國,其傳入中國的時期,是較其他的美洲起源的作物為早。所謂西番,就中國本部而言,似亦包含著雲南與西藏緬甸接界的部分。在該一地區,如上所述,在明初,可視為已經是栽培著稱曰玉麥的玉蜀黍的一個系統。萬曆雲南通志、萬曆大理府志的記載,是指示著玉麥的栽培範圍甚廣,這應是有其歷史的背景的。
明末,雲南省有很多關於玉麥的記載。清初的雲南府志(1696),在玉麥外亦有西番麥之名,二者大概是有著形態上的差別,據此可知西番麥之名,大概亦很早已經通行。在此附帶要說的,是筆者對於玉蜀黍由中國的所謂西番地區傳佈至東南地區的推測。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嘗發兵征麓川蠻族酋長思任,這一戰爭延續頗久,至正統十四年(1449)方止。這一遠征軍的主將王驥,據說嘗以蘭茂為顧問,而聽取其計謀。麓川地區,具體地是相當於現在的那一部分,筆者不甚明瞭。至於遠征軍,則是在中國東南部組織,明史王驥傳謂徵集江蘇浙江安徽人員15萬人而編成。後代的揚子江下游地區的記錄中,屢見有番麥,西番麥之名,據筆者的推測,很可能是由該項遠征軍殘存者攜歸的種子所繁殖。據行軍記錄,可推測該一軍隊嘗到達緬甸的中部,甚或嘗到達其北部。當時,該一地區嘗栽培亞洲型(于按,即所謂Persian type)的玉蜀黍,大概是很確實的。但筆者不是說該一地區是玉蜀黍的原產地,祇是以為可能是在哥倫布以前的某一時代,由某一路線,有玉蜀黍的一個系統傳入該一地區。其詳細情形,則尚有待於今後的研究。
原载:http://seed.agron.ntu.edu.tw/cropsci/maize/yu01.htm